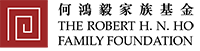一千雙保護唐卡藝術的手
文、圖:Tobias Reeuwijk 翻譯:拾方藝廊 | 2016-05-20 |
用你的肉眼去看東西,跟用心去看,有甚麼分別?而用心去看,又如何為他人帶來平和?
今天的世界看似走得愈來愈快:科技和消費水平以幾何級數增長,導致各地出現資源競賽,過程中甚至引發戰爭。全日二十四小時的新聞報道,讓很多人接收到不同資訊,自然使他們處於較為有利的位置,去幫助弱勢的一群;然而面對鋪天蓋地的報道-弱者受欺壓、違反人權、家庭暴力、天災人禍、環境破壞、饑荒和貧窮等,大家已變得麻木。

佛法很多時說到,五蘊(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)是無常的,而執著它們則是痛苦的根源。若不轉化對五蘊的迷執,就會生起「貪、嗔、癡」三毒,繼而不斷於輪迴中流轉。輪迴這個生死巨輪,「諸苦再再生」,是眾生的必經階段。大部分的佛教修行均著重了解「六識」的緣起性,看清表象背後的本質,好得以活在當下,不管目前處於順境還是逆境。認識真如法性,無論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如何,都能放下身段,協助受苦的眾生,這正是藏傳佛教的修行之途和目標。
按照佛教對現象的理解,人生在世就像海洋:潮汐不斷漲退,其間不時會有驚濤拍岸。大家也許不知道,暴風之中,風眼處最為平靜;浪濤也一樣,就在急升的潮水中心。而且,即使海面波濤洶湧,水面數米以下的水流卻是靜態的。從岸上觀察,驚濤駭浪真的很危險,但是有經驗的滑浪者卻會視之為磨練技巧和尋找樂趣的良機。不丹的修佛者亦然:透過密集的修行,試圖調伏混亂的思緒,看破障蔽自心的煙霧和幻象,轉化自己的感官。


在太平洋掀起的白頭巨浪數千哩以外,一批僧人在各自的「宗」( ,rdzong,意即寺廟建築)裏修行,直到他們往生到極樂彼岸去。不丹的面積跟瑞士差不多,人口不足一百萬,分散居住於喜馬拉雅山區。這個北部與中國、南部與印度接壤的內陸小國,只是地圖上的一小點,要保持主權和文化身份絕不容易。不丹擁有豐富的文化傳統和優美的自然環境,因此被譽為「最後的香格里拉」(The Last Shangri-La)。若不是擁有前者,不丹將難以維持獨立(不論是在任何層面上)。
不丹大部分令人嚮往的傳統都跟佛教修行有關,而國人的確大多信奉佛教。不丹從來沒有給佔領過,過去一直奉行鎖國政策,不歡迎外國人進入。直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初,才准許第一批遊客入境。不丹文化可說是其最重要的資產,也是推動國內生產總值上升的最大力量─但是這種文化正面臨消失。在不丹持續發展及開放經濟的過程中,她的傳統風俗卻在急劇轉變。
在不丹,唐卡畫像無處不在,但也是國內文化衰落的象徵。唐卡以佛教諸神的形態,以及不丹的歷史、文化和傳統為題材。當地人相信,舊唐卡盛載著古代大德的加持,對於觀想修行大有好處,有助長養菩提心。可惜的是,越古老的唐卡越難以保存,而當時的工藝水平,今天難以重現。

不丹僧人一直不懂得如何保育這種消逝中的神聖藝術,直至修復大師Eddie Jose在2004年初開始訓練了一群僧人才見轉機。當時Eddie邀請這些僧人到夏威夷,參加為期六個月的密集式工作坊,傳授他們修復唐卡所需的基本技巧。Eddie曾在東京學習修復傳統日本藝術品達十一年,是世界知名的修復專家,專門為私人收藏家及機構修復亞洲區的藝術品。2000年,Eddie跟他的日本上師首次造訪不丹,初次想到成立該國首個修復工作室。他們在當地逗留了一周,正準備前往機場離開之際,Eddie接獲一名政府官員來電,請教他應該怎樣修復不丹國家博物館收藏的一些唐卡卷軸。他檢視了那些卷軸,作品的美態和殘破程度,同樣令他大為震驚。在飛返夏威夷途中,他不斷回想起那些懾人的畫像,以及思考自己可以怎樣幫助僧人保存他們神聖的藝術作品。
Eddie對僧人的訓練就由夏威夷那個工作坊開始。他們在六個月內除了學習藝術品修復外,也享受到生命中很多美好的事物,包括滑浪、吃意大利薄餅,甚至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迷途。Eddie承擔了各僧人在當地的開支,並且擔任計劃的投資者,因此他需要定期注入資金,以購買昂貴的顏料和修復工具。為了籌集往返夏威夷的旅費,以及不斷上升的物料開支,Eddie提議僧人在滑浪板上繪上傳統的不丹風格圖案,一共八款,結果在市場上大受歡迎。僧人完成修復速成班後,便返回不丹。




在青少年時期,我跟大多數人一樣,很容易受朋輩影響,做事不會深思熟慮,只憑一時衝動。我媽媽以為,給我一塊畫上傳統不丹圖案的滑浪板,可以令我更懂得欣賞藝術,也會令我變得更為沉著。我雖然感謝媽媽送的這份好禮物,但起初心想這塊板的價值,只在於它所用的物料,以及板上那條龍的美感。我對於僧人、不丹,或為甚麼他們會在我的社區裏出現,全沒興趣。我不能將那塊有龍圖案的滑浪板放進水中,於是它就在我的房間中逐漸封塵。不過那塊板擔當的角色卻愈來愈重要,不再只是美學上的功能,而是在我的腦中形成一個空間,讓我在滑浪狂熱中,漸漸萌生佛學和正念的種子。十年之後,機緣巧合,Eddie在找尋一些東西來記錄他於工作坊所做的事情。當我聽到「紀錄片」和「不丹」等字眼,便毫不猶豫決定參與。
自從舉辦了第一次工作坊後,Eddie每年都前往不丹兩個月,而且直至目前,他仍然提供修復所需的所有物料。他繼續是修復計劃的主要資金來源,多年來也致力創辦財政上自負盈虧的修復工作室。為了支持Eddie的計劃,不丹政府給予僧人一個辦公室,供修復唐卡之用。


四年前,一名不丹皇室成員Ashi Kesang偶然加入了行列,跟僧人和Eddie一同接受培訓。他們領悟得很快,但是修復一幅唐卡要經過很複雜的工序,需時半年至一年。而不丹有逾二千家佛寺,每一家都有六、七十幅唐卡藏品,修復工作看似不可能完成。事實上,即使Ashi Kesang加上四名僧人每年工作365天,每天八小時,也要八千年才可以修復所有唐卡─這還沒有計算當唐卡修復後,它又會立即開始遭歲月侵蝕。
要修復所有破損了的唐卡,近乎是神話。Eddie的最終目標並不是這樣,而是工作室能自負盈虧,讓僧人和Ashi Kesang可以收費修復全球私人收藏的唐卡,然後將收益用來修復全國佛寺中的唐卡。在生與死的混沌巨浪中,唐卡修復是維持不丹文化身份的關鍵。若能拯救這門神聖的藝術,觀賞者就可以學習用心去看,而不是單用眼睛去看,同時可以讓將來的觀賞者了解到不丹深厚的歷史。
Eddie和眾僧人邀請我到不丹開始拍攝我的首部紀錄長片《千手大師》(1000 Hands of the Guru),至今已經三年了。現在,我們已將整個修復過程記錄下來,呈現出修復一幅作品所需要經歷的每個細節,還有整支唐卡修復隊伍在工作室所花的心血。對我來說,製作這部電影的過程是一堂課,讓我馴服自己的外在感官,專注手頭的工作,接受世事無常,並且明白事情不能只看表面。